消失请问各位兄弟,白条加油额度可以取现吗?怎么套呢?
|
现代舞剧场《消失》,是舞蹈家侯莹受2021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创作的,也以此纪念她的舞团成立十周年,不久前在上海国际舞蹈艺术中心大剧场完成首演。 规则,丛林,轮回 身体不撒谎。身体状态是内在精神的本能而直接的外化。表现在舞台上,演员之间的位置和交互关系,抚摸、疏离、纠缠、对峙等,隐喻现实对象之间的关系存在,成为大小社会和情感方式的艺术再构。 侯莹现代舞新作《消失》,选择击剑竞技的日常为切入点。群舞以剑锋敲击舞台为发端,时钟般滴答作响,此起彼伏,似众剑者的宣战预警。随后的一片沉寂中,两位舞者步步逼近,带出无名的紧张感。然而,随着步法的不断重复和多组舞者的回环往复,悦耳的敲打乐音介入,谐和中带着不谐和,紧张感逐渐消逝或曰被“放下”。舞段演变为集体有意识的规定动作,一切竟优雅了起来,与电子乐的玄虚氛围形成互动,特别是两组舞者的看似对峙、实则交错而过,视觉差生成意趣别致的游戏感、仪式感,走进“和合”状态。 日常的基本功法训练得以舞台再现,舞者矩阵的纵横移转与机械动作,进攻、躲闪、击杀……严苛的技法在高度统一的规范下,肢体动作不断重复,演绎出几分喜感。“竞技”似乎仅剩表象,只是单纯的技术存在——貌似“花架子”的煞有介事。突然让人产生质疑:原以为激烈的无情争斗,竟建构在如此温情的“约定”之下。至此,荒诞意味淡淡溢出。 在条块分割的布光中,剑者锋芒渐显。较量伊始,一切尚在从容和规则下,当单纯的剑体摩擦声成为主音,气氛和表达趋于紧张和凝重。 当黑色二道幕升起,泛蓝的天幕映衬出一副跷跷板,《消失》的剧场寓意开始显现。争斗在慢速的肢体动态和不稳定的摇摆中,被加剧,被放大。出自法国戏剧《大鼻子情圣》的一段法语旁白,语感比文字重要,有了时光、语境、情绪的带入感。不断加强的弹拨乐摩擦音、电音效果,与剑体撞击声浑然一体。 这种“放大”和情境氛围,让舞台变成了剑者的微观心世界。一个貌似自由博弈,却是“默契”下竞争的、饰演的、冷酷的混杂视野,被徐徐展开。 慢速的动作,打开了表象之下的细微,舞者在击剑的典型动作中夸张变异,给出了心理暗示,诱使观者在细微中感受剑者的不安和纠结。击杀、恐惧、提防、试探等行为在同一时空中存在,竞技规则退隐。低音震颤,舞者头颅和身体上的几把剑,像是扎入又像长出的苍凉;八音盒清脆乐音下,“千手观音”似的组合动作,不再是慈佑而是进击……一幅幅丛林规则的画面,令残酷感滋长、文明感淡出,构成多重心态,或许也是多重人格的冷酷写真。随之而至的身体托付、萦绕和宗教祭祀般的游走,在长音和声与不安定的短散支调纷扰里,完成了一道轮回。 《消失》选择击剑作为基本肢体语汇,初看上去很讨巧:现代击剑运动是优雅的竞技,有刺激的动作性和戏剧性,也有安全的“文明规制”。施之舞蹈化处理,视觉、节奏、空间、矛盾张力都占有天然的创演优势。但若就是满足于此,可能只会是行业表现作品或以“寓教于乐”为名的励志宣传剧。侯莹的《消失》立意并不存在于这类表象中。她和她的舞者们,把剑锋当作刺破地壳的钻头,穿过青草野花,穿过陈腐的积土,刺透重重叠叠的人性岩层,凿出浑浊的岩浆。 剑,面具,跷跷板 《消失》的后段,进一步由现实介入内心,赤裸裸起来。“规则”成了表面化的伪饰,间或被打破,剑者之间、剑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沉郁飘忽,不稳定且不可预料。 当一组舞者把剑倒提在手中,似钟摆又似摇曳的祈祀酥油灯;另一组却剑指心脏咄咄逼人,又集体转为即兴把玩般的花样甩荡,分裂,无奈,纷乱。被缓缓拖出的两爿硕大面具,欲合而不合,是为点题。躺在面具下的残喘,剑从里向外刺出同时从外向内刺入的决绝,以为会相拥却相悖而去的一丝寒意,撕开了“关系”的脉脉温情,划出道道裂痕,不可弥合。舞者凝视的一瞬间,视觉与玛莎·葛兰姆现代舞团《悲歌变奏曲》里那段生死一线的深刻记忆交汇,那一个的回望难舍离与这一个的秋风悲寂寥,异曲同工,都浸透了对生命的怆惋。 剑、面具、跷跷板,三者作为现代舞《消失》中的物体存在,是侯莹匠心的重要表达。剑,亦是自我,它的摆动、冲刺、躲闪,就是自我的适应、观察、进击与防护。面具,代表着看见与看不见,也是观演之间的心理屏障。观众看不见的,是剑者鲜活的面孔;看得见的,是厮杀的冷酷和力量刺激,满足于“假性生死”的游戏;剑者看得见的,是观者的兴奋与剑花飞溅;看不见的,是观者的血腥欲求和原生野性的抑扬。跷跷板,本是儿童嬉戏的天真道具,却承载两位剑者的剑锋相对。守衡与失衡,成了矛盾世界难以调控的摇摆,是社会生存中无法回避的攻击和抵御本能的化身。 现代舞《消失》,是内心野性与文明之约的人为间离,宇宙空间里的真实戏剧。野性并不会因为文明的介入和界定而消失,文明并未让生物链条的你死我活走开,人类的社会规则在这些面前,近乎伪善和绵软无力。我们一直坚持的改变企图,只是在压制和藏匿残酷的真相,它们从未消失,从未真正改变。 光,曲,民族语汇 造型光的条块式风格,就像是现代文明对丛林法则的制约,时而明晰,时而淡入淡出,时而交叠昏乱,突出了不同情境和剑者的不同状态,也是强烈的心理暗示,引导观众从直观的清晰与混浊表象,走进似是而非和不断扰动带来的精神不安。 《消失》的作曲Cornelius Berkowitz与声音设计Kevin Polak功不可没,现实的敲击碰撞声,夸大的噪音摩擦音,泛音和电音,无调性的基调,都给了作品灵魂般的支撑。剑身碰撞的金属声,开始是悦耳的,在进入搏杀前的那一瞬间,猛然间夸大刺耳的那声摩擦,穿透耳膜,穿透身体,让神经痉挛。 侯莹在《消失》里的民族语汇意识,也许不是刻意的,却是很有意味的自然流露。当一位女舞者手抚竖倚在胸侧的长剑,头部倾侧与翘起的手势,娇弱感透着中国戏曲旦角的妩媚,但美韵乍现,迅即被其他舞者的介入而冲走。《三岔口》样的打斗,像一面经验的镜子闪倏即逝,留下似曾相识的矛盾张力。 最后的画面落在了寻求平衡。剑者踽踽走向未知,踯躅于支点之上,是对世界的敬畏、向往、探试还是无奈,或是兼而有之?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可以看到,一切都没能也不会停滞在某个时空,始终在走上或走下。我们无法放弃自己,无法放弃有些无力却不得不继续的文明进化 |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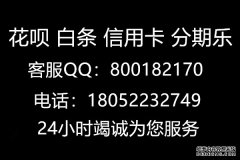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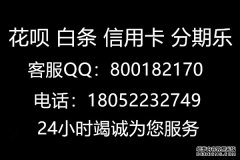


评论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