挣脱“命运漩涡”的黄国平与小城仪陇的教育求变
|
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南端,一个名叫炬光的小村,被黄国平的博士论文致谢意外“点亮”。 2021年4月,仪陇进入雨季,黄国平出生长大的老宅隐藏在猴坪山脚下的云雾里。这里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,用来搭台阶的老岩石参差不齐,像是整块搬来没有细致加工过;屋顶的青瓦薄薄的,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凶猛的雨势,黄国平童年的“保留节目”——“用竹笋壳塞瓦缝防漏雨”已经许久没有派上用场了。 人生的剧本,黄国平起手拿到的就是“困难”模式,他用二十二年的时间,走出山坳,走出了一条寒门学子靠知识改变命运之路,“这一路,信念很简单,把书念下去,然后走出去,不枉活一世。”
2021年4月,仪陇县炬光村,黄国平以前的家和他伯伯现在的家。新京报见习记者 郭懿萌 摄 在黄国平风雨泥泞趟过求学路的同时,他的家乡仪陇县也没有停下教育求变的脚步。 “仪陇以前在教育方面吃过亏,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,新县城建立的时候,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。”仪陇县委一名干部介绍,从2017年以来,仪陇累计在教育方面投入36.5亿元,几乎每隔一公里,都会有一个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。 黄国平母校仪陇中学的副校长希望,“孩子们通过学习知识飞出大山,在祖国各地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 “那个放牛的娃儿要出来了” 炬光村有一条新街,一条老街,在铺着柏油马路的新街背后,穿过一条泥泞小路,隐约能看到几十年前的“旧影”。 几栋墙壁斑驳的老房子立在路边,砖砌的外墙,竹编的篱笆围栏,缝隙中糊着伴有稻草的泥巴,屋顶一层薄薄的瓦,墙边斜倚着几捆竹竿和木柴。当地人说,这是过去仪陇常见的民居,已经很老了。
2021年4月,仪陇县炬光村老街上的旧屋。新京报见习记者 郭懿萌 摄 黄国平的老宅样子差不多,位置还要更高一些,有着一二百米的垂直落差。这条通往黄家老宅的山路,近些年被政府修出了一条“便民路”,村民可以拾级而上,但最陡的地方,坡度还是能达到45°。 二十多年前,人踩在泥巴上歪歪斜斜的就是一条路,黄国平和发小黄军就是从这走向炬光乡小学,赤着脚踩在泥里,一步一个脚印。黄军记得,碰上下雨天,“哧溜”,脚底一滑就摔个屁股蹲儿,黄国平描述,“雨天湿漉着上课,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。” 打赤脚,是附近乡镇80、90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永光镇党委书记王伟荣回忆,孩子光脚上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很普遍的现象,“我小时候也经常打光脚板,脚上沾到了泥巴,放到水里涮涮干净,到教室再把鞋子穿上就行了。最奢侈的时候就是穿双解放鞋。” “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。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战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。”这些都差点成为压垮黄国平的最后一根稻草,那不仅是“人后的苦”,更是无法维持的“人前无比脆弱的尊严”。 黄国平家里穷,在伯伯黄世俊的记忆中,侄子上学比别的孩子都晚,直到七八岁才读小学。那时候,收入来源之一是自家的三亩庄稼地,“种些玉米、红薯、油菜”,除此之外,黄国平的父亲有时间就给别人做小工,“上世纪九十年代,做小工一天只能赚1块钱”。 17岁时,黄国平失去了父亲,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在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去世。同年,婆婆病故,下葬时仅有一副薄薄的棺材。更早在五年前,黄国平还是个12岁的孩子时,母亲就离开了家。 抓黄鳝,成了高中前黄国平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。夏季白天天晴的夜晚,九、十点钟,村里的娃娃们就结伴去水田里抓黄鳝。两根竹子用钉子串在一起作为工具,夹到黄鳝后“啪”地一下甩到背后的背篓里。夜里抓黄鳝、周末钓鱼,这些孩子们的童趣,却是黄国平的谋生之道。 比起用脚一遍又一遍丈量方圆十里的水田和小河,能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,可以算是黄国平“最开心的事”。 在村民黄仲印象里,小时候家里经常停电,各家都常备着煤油灯。黄军记得,黄国平家里没有电灯,“他就每天熬着煤油灯做作业”。 一灯如豆,照亮了黄国平的求学路。家徒四壁,墙上最珍贵的是一张张奖状。“贫穷可能让人失去希望”,黄国平在致谢中写道,“如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状,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,我可能早已放弃。” 从炬光乡小学,到仪陇县中学,从重庆的西南大学,再到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,黄国平终于实现了“走出大山”的愿望。去北京读书时,他带走了贴满一面墙的奖状,伯伯还记得,那些奖状“卷起来一大卷”。而从小到大的课本,黄国平特意将它们装在一个木箱子里,保存在伯伯家二楼,他要留作纪念。 黄世俊清晰地记得,一个黄国平读研期间的假期,叔侄俩放牛的时候,黄国平对他说:“黄家湾那个放牛的娃儿要出来了。” “高中时班里的电脑都是他维护” 仪陇多山,沟壑纵横,道路上上下下,从炬光村到最近的永光镇,还要走近十公里弯弯绕绕的盘山路。 2004年,黄国平升入仪陇县中学。当时从村子到老仪陇县城的路很漫长,每天只一趟大巴,单程近三个小时,路上的泥土混杂着石子,磕磕绊绊地纠缠着这个山坳里走出去的娃儿。
仪陇中学老校区。受访者供图 仪陇中学听说了黄国平的情况,免除了三年的学杂费,还牵头寻找爱心人士资助他。当时的食堂负责人胡元明接过了爱心接力棒,负责黄国平高中期间的生活费。胡元明的家也成了周末、寒暑假期间黄国平的落脚点——为了节省15元一趟的车费,黄国平很少回炬光村。 胡元明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资助黄国平,可能是因为二人同为仪陇中学的校友,也可能因为都是出身农村,“我觉得没啥子。” 看到“博士论文致谢”的时候,饶彬隐隐猜到了文中的主角,作为黄国平高中时期的班主任老师,饶彬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,觉得触动内心,“写得真真切切”。 饶彬还记得黄国平在高中时期就展现出了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,“当时我们和成都七中合作直播教学,黄国平在试点班里,班里有个电脑,基本就是他在维护,修好修坏都是他,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修坏了他也能重新修好。” 2003年,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,仪陇中学引入了成都七中网校的直播教学。直播班每天全程连线成都七中的课程,仪陇中学的老师则在课下再进行辅导。副校长周乐强介绍,“这样直播班相当于有完整的两套全学科老师辅导。” “32个学生,一共22个上了本科,其中9个一本。”这个数字周乐强记得特别清楚。“试点之前,黄国平那个班成绩并不突出,按之前的经验,能有一个同学上一本都很不容易,但是连续上了三年直播课后,一下出了9个一本。”现在每个年级还有两个班在上直播课,全校一共六个直播班。 第一次高考,黄国平考上了省内一所本科师范类学校,“我们当时觉得他家庭条件不太好,读师范毕业了很好找工作,但他觉得与自己志向的专业不一样。”饶彬回忆。 他对计算机的热爱恐怕要追溯到初中时期,炬光村村民黄小林把黄国平和他计算机启蒙老师的关系形容为“弟兄”,“他读初中的时候,邱老师带着他去条件好的地方,带他学修理计算机,带他和其他条件好的孩子一起参加计算机培训班。” 在绵阳南山中学复读一年后,黄国平考上了西南大学。黄世俊记得当时他劝说过还想再复读的侄子,“万一你思想懈怠,怕是之后考学更难。” 听从了伯伯劝说的黄国平开启了他的大学生涯,“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,胃溃疡和胃出血也终与我作别。”在西南大学,他拿了两年国家奖学金,参加了9次数学建模比赛,获得了美国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…… “仪陇不能再吃教育的亏了” “教育”二字是仪陇县的干部们常挂在嘴边的。 仪陇县委一名干部形容,“2015年之前,全县上百万人口中,有26万人连用水都困难。”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直到2018年才脱贫摘帽,之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谓是有心无力。 黄国平的很多同龄人都有和他类似的经历。在他们的成长、求学过程中,还要兼顾做家务、干农活、勤工俭学,“孩子帮父母分担理所当然”。 仪陇县另一个村里长大的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,当时乡镇农村的大多数小学和初中都有“农忙假”,五月前后会放一周左右,大一点的孩子帮忙插秧,小一点的在家做家务,做饭端给田里的大人们。平时写完作业还要帮家里去山坡上打猪草,裹来喂猪喂牛。 而他印象最深的是乡上小学的操场,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,比较困难的小学操场里都是泥巴,下雨天很滑。孩子们就把街边废弃的瓦砾背来敲成小颗粒,家里烧完的炭渣也背来一起撒在泥巴地面上铺平,大家齐心协力用铁锨把操场“面起来”,“这样铺上去不积水,还软和,穷的时候只能这样办。” “仪陇以前在教育方面吃过亏,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,新县城建立的时候,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规划。”仪陇县委一名干部介绍,从2017年以来,仪陇累计在教育方面投入36.5亿元,几乎每隔一公里,都会有一个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。
仪陇县新县城。受访者供图 2014年,炬光小学开始翻修,前年竣工。“以前的操场就是在地面上用水泥硬化了场地,只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,翻修后铺设了橡胶操场,还新建了两个篮球场。”黄仲说道。 位于新县城的仪陇中学新校区是老校区的近3倍大,面积可堪比大学,2020年9月,迎来了第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近5500名学子。去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地方读书,这是在乡镇工作近20年的王伟荣近些年感受到的变化,“00后比80、90后好很多,以前的娃娃相当于是被隔代人‘散养’长大,现在的父母更重视教育,会关心娃儿有没有出息,怎么能提高教育。” 如今,仪陇中学的老师们不用再四处求助爱心人士资助贫困学生,国家助学金、仪陇中学校友创立的“西瑜助学金”、“滋蕙计划”等扶持措施可以使像黄国平一样的寒门学子的求学路走得更加顺畅。
仪陇中学新校区大门口的一群飞鸽。受访者供图 仪陇中学新校区的正中央是一群飞鸽,副校长周乐强将这理解为一种祝福,“希望孩子们通过学习知识飞出大山,即便不再回来,也可以在祖国各地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 新京报见习记者 郭懿萌 发自四川仪陇 编辑 刘倩 校对 卢茜 |



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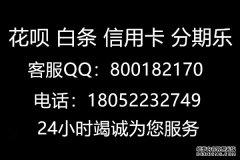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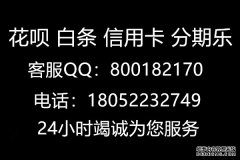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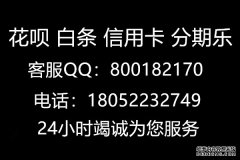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列表